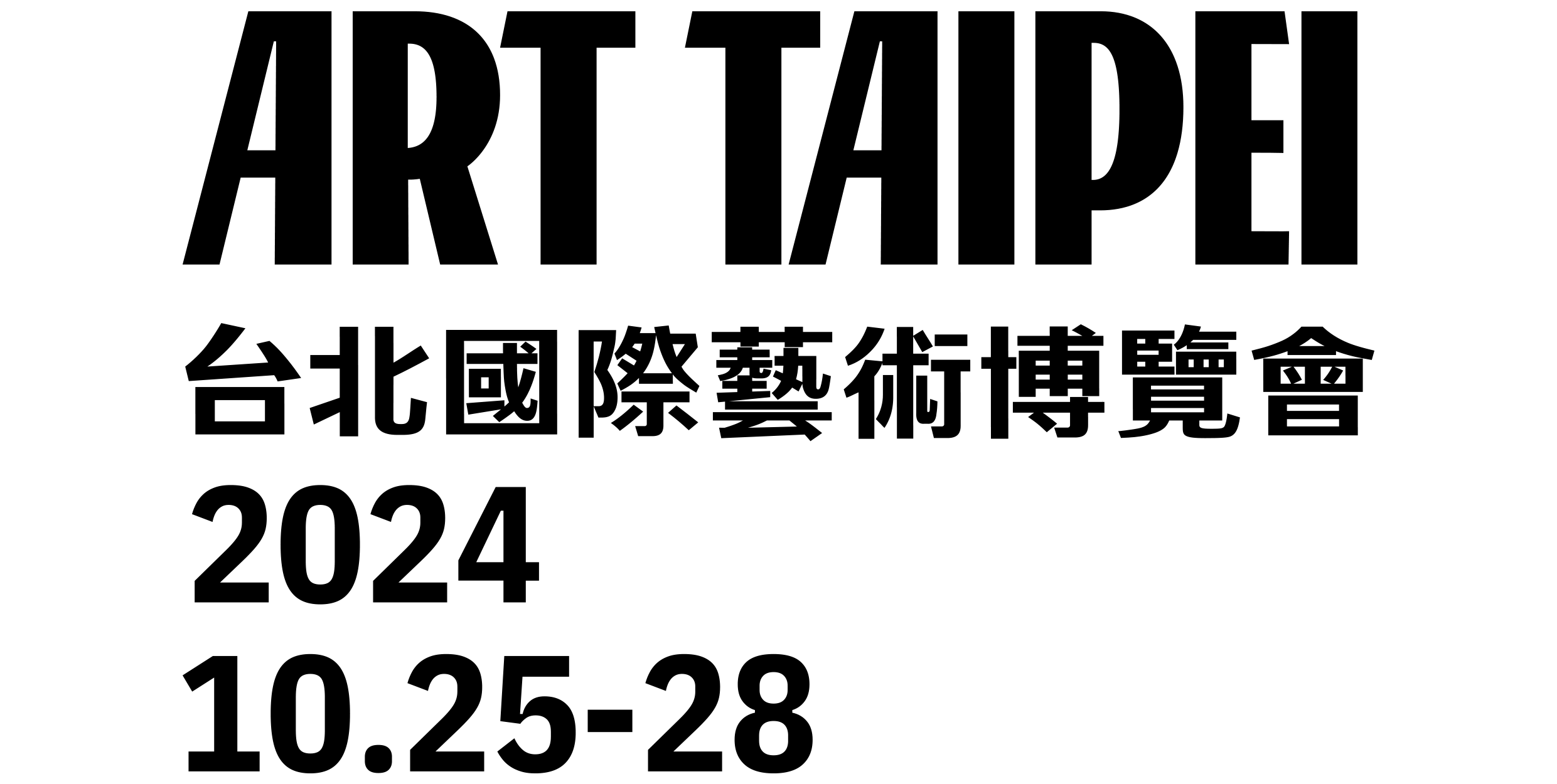中原千尋
Vernal Room Drama
壓克力彩畫布
80.3 x 65.2 公分
2024
生活小劇場—中原千尋的「寓意畫」
文/陳貺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1990年出生的日本畫家中原千尋,畢業至今已有近十年的職業生涯,她的創作也隨之發展出越來越濃烈的個人色彩。乍看之下,她的作品及創作過程很類似插畫或動漫:從人物角色的設定,到充滿童趣的造形,到豐富卻又不失統整的色彩及構圖安排,再以蛋彩或水彩、壓克力彩等水性材料,以充滿女性特質的筆法細細地描繪而成。畫面中充滿著玄奇古怪的人物與動、植物,彷彿從宮崎駿或新海城那滿溢想像力的奇幻動畫中走出。雖然有不少藝評家強調她與插畫及動漫藝術等流行文化的關係,也有不少人提到日本江戶時代的琳派以及該派始祖尾形光琳對她的啟發,但我更想強調的是她與西方藝術史傳統「寓意」(Allegory)的關係。
中原千尋曾自述:「有時在我的腦海中會浮現像短片一樣的小故事,又或者會浮現關於畫面顏色的設定。」而這些腦中小劇場的來源乃是日常生活,以及她身在其中的敏銳觀察:「到目前為止,我都是把真人變成人物,然後把他們封裝在畫裡。」這種將日常生活的情境轉化為藝術作品的手法,我們稱之「寓言」(Fable)。而她也曾自述當年自我懷疑能否成為職業畫家時,正是透過參照《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創作出〈兩種選擇〉這幅作品,並因而得到了救贖。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她的創作與「寓意畫」之間的關聯。
所謂的「寓意畫」發源自古希臘羅馬時代,寓意畫家從既存的情境出發,以圖像的方式創造出寓言或譬喻(Parable),並藉以帶出圖像背後蘊含的道德寓意。藝術家可以取材自自然(寓言),或人類生活的場景(譬喻),但不論從何處取材,皆以謎語和寓言將元素組合起來,建構成一個超現實的情境,從而將抽象的思維變成可視的人事物。而被謎團與象徵籠罩的寓意,唯有在觀眾鍥而不舍的探索、解碼與解讀之下,才能被抽絲剝繭、徐徐展開。這是觀眾們最大的樂趣,也是他們之所以對寓意畫著迷的原因。但在解謎的過程中,藝術家亦須提供蛛絲馬跡來引導觀眾,因此這既是一場藝術家與觀眾的對弈,也是一場二者協作的意義書寫。寓意畫自上古流傳至今,由於具有賦予畫作意義,並將繪畫與其他領域,如文學、戲劇、詩等連結的功能,一直是畫種中最為高貴的,但也是最困難的,因為畫家必須尋找出可引人聯想的屬性和元素,並收集大量的人物、動植物、物體、姿態與動作,而參與寓言的還包括繪畫時的色彩、材料、筆勢與肌理等等。
荷蘭畫家波希(Bosch, 1450-1516)是個中高手,他於1500年所繪的三連屏巨作〈享樂的花園〉呈現出北方文藝復興中的怪異畫風和不可思議的想像力。作品中出現的人物、鳥、水果等元素似乎是欲望的象徵,隱喻腐敗和墮落的人類似乎無得救之可能,此作隱隱透露著悲觀主義。至於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米羅(Juan Miro, 1893-1983),更是從他「細密畫」時期的作品〈小丑的嘉年華〉開始,即在畫面中布置了緻密的「細節」,每一個元素與符號無不貢獻於畫作意義的傳達,同時卻又能達到高度的詩意。
我們很容易看出中原千尋的「寓意畫」如何繼承這些大師的脈絡,她不但在構圖上同樣採取充滿細節的「滿佈式」構圖,也曉得如何將所有的元素,包括造形、色彩與材料,編寫成一首複雜卻和諧的交響曲,傳唱著那些她從生活中體悟而得的想法與故事。例如她2012年的巨大畫作〈音樂人〉中「紅色盔甲的少年」必須透過幼時以愛情創作的寶物與唱歌來通過18歲成年儀式,而紅色的「省思球」則隱喻「無法在儀式中成為大人的居民」晚年的空虛生活;「變長的笛子」像是「魔笛」的翻版;「紅白樂隊」的合奏則為了療癒弱小又悽慘的人類。這件作品既有波希的怪誕畫風,也浸染著同樣的悲觀主義,當然更是畫家自己被迫成長時的徬徨與焦慮之具現。至於2014年的〈獅子狂想曲〉則像米羅的畫作一樣,以太陽和獅子的形象將自己塑造成狂想畫面中的主角,奇幻之餘同時也彌漫著詩意。至今中原千尋還繼續著其永無止盡的創作之路,她那些2022年來臺灣時信手繪在報紙上的手稿,多少揭示了她的創作過程,而以中元普渡為題材所繪的奇趣畫作更是令人莞爾。十年來隨著她生活經歷的擴充以及持續不懈的努力,中原千尋平息了無法通過成年儀式的焦慮,並且正從當初羞怯的藝壇新人,蛻變成堅定且備受期待的優秀寓意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