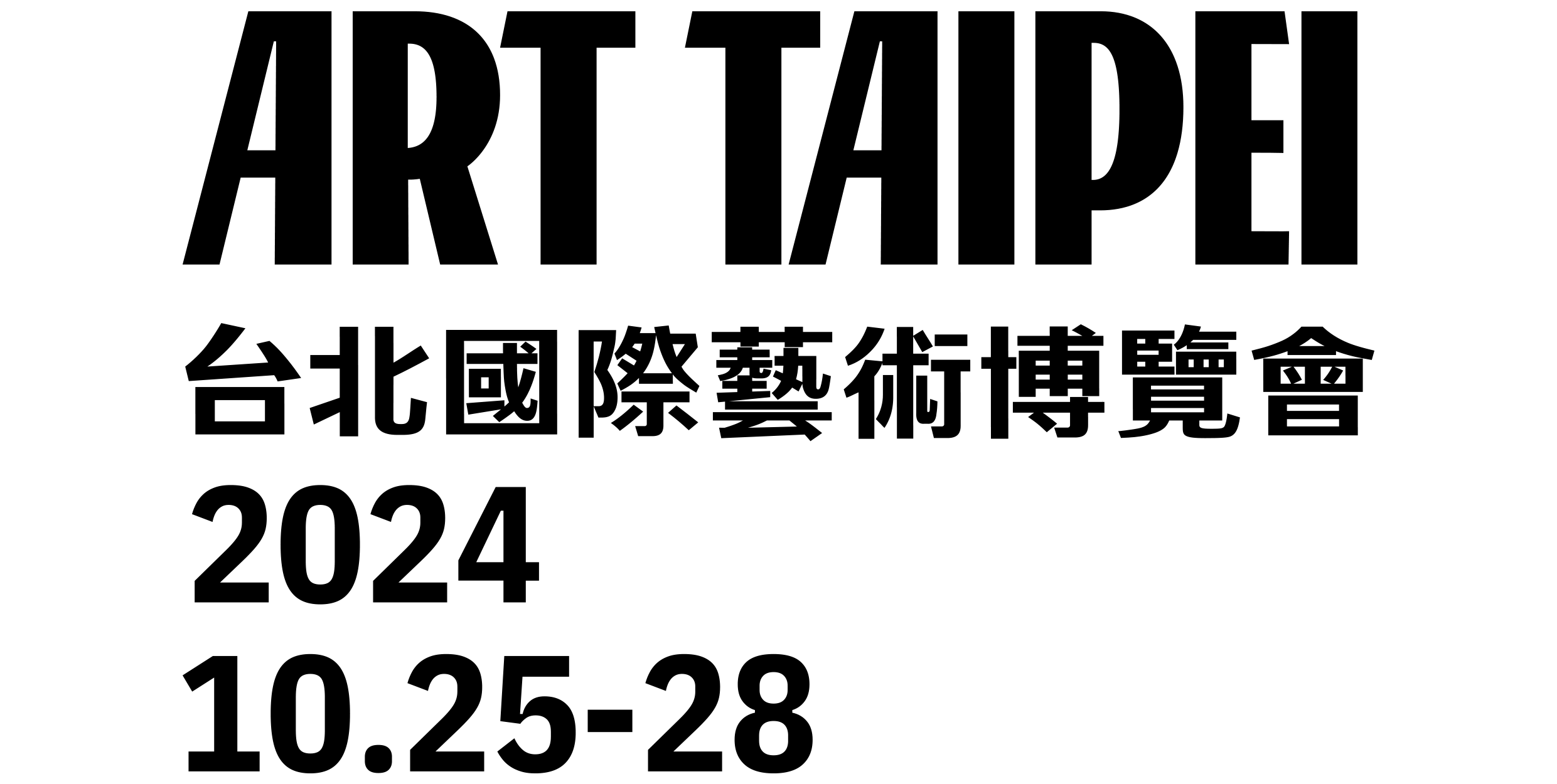原住民族藝術特區迎來第五屆展覽,將於2024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中隆重亮相。此次展覽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和亞洲藝術中心共同合作,展出四位原住民藝術家——伊誕.巴瓦瓦隆(Etan Pavavalung)、林安琪(Ciwas Tahos)、魯碧.司瓦那(Ruby Swana)和瑪籟.瑪卡卡如萬(Malay Makakazuwan)。
本次展覽深入探索這些藝術家在不同關係和文化脈絡中的創作詮釋:林安琪的作品是對文化和性別認同的探索,利用她的身體作為媒介來追尋語言和文化上的位移經歷,並尋找新酷兒理解形式;魯碧.司瓦那透過阿美族文化,探討靈性與自然神性的神秘連結;伊誕.巴瓦瓦隆的藝術創作,寄寓深刻的文化主體性格,也具對社會、對生態關懷的反思,而瑪籟.瑪卡卡如萬則以裝置藝術結合自然素材,將卑南族文化與現代視角融合,透過傳統神話與族群歷史的脈絡,表達她對當代社會的省思與原住民身份的自我認同。本次展覽涵蓋了多種創作媒材與技法,充分展示了原住民藝術家在當代語境中的創新實踐與深度藝術探索。
當代藝術舞台上的原民現身:2024 MIT 原住民族藝術特區
文/徐文瑞
獨立策展人、評論家
ART TAIPEI 的 MIT 原住民族當代藝術區塊於今年 (2024) 進入第五屆,這個由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與台北藝博的合作項目,也從初始階段的觀望期待,如履薄冰,逐漸演變成今日眾所矚目,成績斐然的展覽。這過程當然不是旦夕成事,一蹴可幾的,綜觀這一段歷史,至少從 1980年代原住民族運動隨著台灣民主化運動風起雲湧的日子開始,原住民當代藝術就已經像如影隨形的幽靈,漂浮在台灣的文化天空,這期間國內的美術館像高雄市立美術館、原住民族文化園區以及主要策展人,都扮演著官方與民間機制的扶植推手。過去十多年來,原民藝術家人數逐年成長,創作也更加豐富成熟,遂得以在國際上受到關注,受邀參加世界上重要的國際雙年展、三年展,例如澳洲亞太三年展、雪梨雙年展、橫濱雙年展、光州雙年展,甚至威尼斯雙年展和德國文件大展,當然,國內的台北雙年展與台灣美術雙年展也不例外,已經是原民當代藝術家大展身手的舞台。
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潮流幾乎是全球文化的新趨勢,並非台灣所獨有。其實,至少從1990年代開始,上述幾個國際上赫赫有名的雙年展,去殖民主義、環境不正義之下的原住民處境、當代新自由主義對在地文化的持續破壞等議題,就一直是展覽的核心關懷。在這氛圍下,「原民性」可以說變成了近年來的「時代指標」(儘管原住民有時候稱為第一民族或土著,但不同地區或國家,則不承認原住民的概念,而僅以少數民族或其他代稱,無論如何,某種殖民形式,土地的流離失所和資源的剝奪,強制的同化等,可以作為全球原住民族的共同標誌)。
就以威尼斯雙年展為例:2019年,因紐特的 Isuma 團隊代表「加拿大館」,探討原住民的強制遷移。接著,因疫情而延後的2022年威尼斯雙年展,則有藝術家團隊將北歐館變身為「薩米館」,讓這個散佈在北歐和俄羅斯的原住民族得以透過藝術表現向世界說話。同年,原本「台灣館」也是以原民藝術家作為代表,可惜因藝術家深陷醜聞而被取消參展資格,令人扼腕。(原住民藝術家代表殖民者的國家參與國際展覽,原本就是一個政治和倫理的態度,本身就值得討論,但除了國家和民族之外,藝術也涉及更根本的道德議題:藝術家可以超越個人道德,例如身體自主、性別正義等標準嗎?)
原住民現象一直延燒到今年,正如一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絕非一兩個單獨事件所構成,今年 (2024) 的威尼斯雙年展,就由北美洲第一民族 Cherokee 族後裔Jeffrey Gibson 代表「美國館」,注意,美國評審團肯定深知這個舉動具有象徵性的意義,由美國所代表的墾殖殖民主義 (settler colonialism) 及其當代帝國主義,終於把帝國、國家、領土、殖民、原民性的歷史與道德糾結,提升到藝術的層面來面對。同時,繼2022年加拿大的「因紐特館」之後,2024年則有丹麥所屬自治區格陵蘭的因紐特藝術家 Inuuteq Storch 代表「丹麥館」,他將「Kalaallit Nunaat」疊在該館建築體的國名「Denmark」之上,Kalaallit Nunaat是格陵蘭語裡面指涉 Greenland,本義為「人民的土地」。而澳洲國家館推出原民藝術家Archie Moore,並獲得國家館金獅獎。紐西蘭毛利藝術家團體 Mataaho Collective 受到威尼斯藝術總監Pedrosa邀請參與國際展,也榮獲本年度的金獅獎。
無疑,我們正處於全球原住民族在藝術領域裡面「原民現身」(presence indigene,人類學家 James Clifford 語),長期存在於邊緣地帶,隱而不顯,現在變成了眾所矚目的閃亮金星。其中許多群體在四、五百年的近代歷史中,經歷殖民與壓迫,而在二十世紀的解殖歷程中,並未獲得解放,反而繼續被解放的主流族群所壓迫。這個再殖民的經驗,不僅僅見於台灣的原住民族(包括平埔族群),甚且遍及全世界。消失的落日民族,正在我們的地平線上重新升 起。目前大部分的台灣人知道已正名的總共有十六族,叫得出十族的同胞,恐怕寥寥無幾,或只以為平埔只有一族,且已成歷史名詞,而不知目前尚有至少十族的族人,等待官方正名?平埔族群相關的藝術創作也正緩緩浮現於當代藝術舞台中。
本屆「原住民族藝術特區」共推出四位不同世代的藝術家。
阿美族藝術家魯碧.司瓦那 (Ruby Swana,漢名石瑛媛) 屬於當代藝術圈中壯世代,2002年,她與十幾位藝術家來到台東金樽海灘,這些人有原住民,有非原住民,他們像「天上的一片片雲朵」,不期然飄到一隅,形成一股微氣候,利用海邊的漂流木和拾得物結紮臨時住所,一起創作、自由交談,沒什麼目的。雖只短短三個月,這個意外的聚會造就了「意識部落」的傳奇,二十多年來傳誦於藝術家之間。對比於那時期逐漸興盛的原民創作者,意識部落的人數不多,但卻關鍵地表達了彼時追求精神自由的氛圍,今日看來,那時期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她的裝置作品多屬恢宏大器,直指天心。這次展出她的長期創作「花露初」(阿美語 faloco,意指「初心」,猶如「不忘初心」),那個純淨澄明的心,如她所說「人人有顆純淨的心,萬物隨心舞蹈。」同時特別推出新作「來自大地母親的禮物」,利用植物枝葉印染在羊毛布上,在細膩中露出溫柔的力道。
藝術家伊誕.巴瓦瓦隆(Etan Pavavalung)出身於部落的 Pulima 藝匠家族,他是北排灣族拉瓦爾系的重要文化傳承人,同時也是紀錄片導演、詩人、策展人和教育工作者。他的創作關注族群文化在現代生活處境的繼承與轉化,深具人文和自然生態的敏銳感知,近年來屢受國際的肯定,曾參加澳洲亞太三年展等。他研究口傳文化母體裡 vecik (線條、圖紋、文字) 的美學意涵,利用雕刻刀、壓克力和版畫顏料在木板上施作,獨創「紋砌刻畫」的創作技法與表現形式,根植於排灣宇宙觀中,天地萬物生成的自然紋理,部落生存環境具備的石板所疊砌的棲居空間,以及匠人之心的刻與畫。他認為藝術家是「美的釋放者」,他以「山上的風」和「靈鳥」來形象化這個美學本體論的概念:由於那個永恆存在的靈鳥牽引著萬物的靈動,讓斜坡民族的周遭環境充盈暢然薰風的氣味。
瑪籟.瑪卡卡如萬(Malay Makakazuwan,漢名林琳)是台東下賓朗 Pinaski 部落卑南族人, 屬中輕世代的藝術家,接受過藝術學院(台北華岡藝校)的正規訓練,畢業後留在台北從事電腦繪圖工作,之後進入東華大學初成立的民族學院就讀,加深原住民身份的自我意識。她的發展軌跡見證了一個新世代的原民藝術家如何從幼年在都市環境裡成長,夾在隱身與歧視之間,接觸到台灣解嚴和原住民族正名後的全球化生活型態,同時重新深化自己與原鄉的關係,而作為母親又背負著培育下一代的責任,猶如乘載著部落文化在原鄉和都市之間,堅毅往返而緩慢移動的優雅蝸牛。複合媒材雕塑作品「在這裡存在,也在這裡消逝」是她在藝術圈最初的成名之作。她用一顆顆檳榔作為像素,拼成耶穌/聖母的圖像,垂直懸掛在上,而水平地面上擺設著卑南族祭司專用的檳榔陣,藉由兩種神聖結構的對照,影射殖民過程中外來主流宗教和族群信仰的衝突與協商,但構成元素是手工製的羊毛氈檳榔。檳榔是許多原住 民族在祭典、人際交往、法術的重要媒介。作品「Vetsik 創始的印記」將卑南族神話中人死 之後變為百步蛇、老鷹、竹節中亡者的淚水三個階段,轉化成現代原住民命運的不同面向。
林安琪 (泰雅族名 Ciwas Tahos) 畢業於溫哥華Simon Fraser 大學當代藝術學院,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碩士。越來越多原住民年輕世代藝術家擁有類似一貫的學院養成,但她的經歷卻很特殊,先在北美洲大學念藝術,認識第一民族相關的殖民經驗(當然還包括正規教育的各種技藝),再回到台灣追溯自己的族群身份。她的創作圍繞著自身的酷兒身份,以及家族背景裡的複雜血緣,探究殖民歷史、生命政治、部落神話和多重性別等議題。破印系列《生⇆熟⇆福》啟發自作者為了尋找宗親脈絡,而必須查閱日治時期戶口調查所使用的殖民時期人群分類邏輯,同時,又顯現印刻文化對無文字的原住民所造成的傷害。一個刻有「生熟福」的大印,在機械動力裝置驅動下,烙印著躺在白色平台的藝術家身上,直到她的全身通紅。影射代表父權社會的權印把被殖民的原住民和女性身體標本化、標籤化。作為對抗或和解,「重返土地版」是藝術家把印章帶到原鄉溪流,以泥巴作為印泥,烙印在身上,隨著時間風化,最終乾涸而掉落。象徵著人回歸土地的原初連結。

伊誕.巴瓦瓦隆

林安琪

瑪籟.瑪卡卡如萬